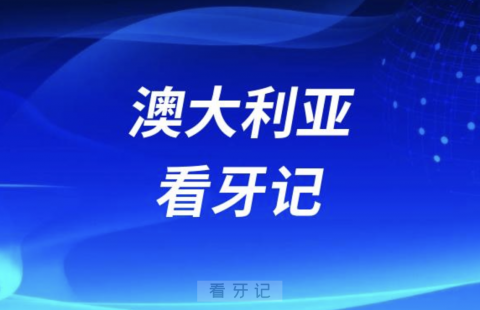我一直以我有一口好牙而自豪,曾经。
从小到大,我的牙整整齐齐,白白净净。跟我熟悉的人,都夸我牙齿好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牙的厉害之处实际上就是特别结实。我吃核桃的时候,基本上都是用牙咬,再硬的核桃在我牙齿的高压下也会化为齑粉。
我小的时候在山西的大山里茁壮成长,当地医院连牙科都没有,也没有什么牙医。我从没有对牙做什么,懒得每天刷牙,我的牙从来没有出过状况。
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抱怨牙齿不好,觉得牙齿应该就是合金钢,怎么可能坏掉!我甚至坚信不疑:我的身体哪里有毛病,牙也不会有问题,哪怕我寿终正寝了,我的牙也会在火化炉里保存完好。
不瞒你说,我第一次听到“智齿”这个概念,还是到了澳洲以后,开始带孩子,听到朋友时时提到他们的孩子拔智齿什么的。澳洲对未成年人的牙齿健康倒是很重视。孩子和同学们都矫正过牙齿,戴过牙套。
我女儿在当地一个著名的华人牙医诊所矫正的牙齿。牙医说孩子的智齿的姿态不好,建议尽早拔掉,以免将来出问题。
我当时还不以为然,问了医生,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智齿问题?现在我都快六十高龄了,牙齿也没问题,该吃吃该喝喝。医生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,我的智齿可能没有长歪,所以不成问题。就算长歪了,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,智齿应该早就停止发育了。只要不疼,不影响其它牙就可以不去管它。我听了就更放心了。
在孩子去美国上大学前,我带她去拔智齿。由于想赶在离开前都做完,所以一次性拔掉两颗智齿。过程貌似很痛苦。做完以后脸是肿的。还要吃抗生素和止痛片。那几天孩子饭都没法正常吃,整天哼哼唧唧,萎靡不振。我当时想,还好,我没有智齿问题。
随后几年,孩子去美国上大学,我搬离华人区,到了墨尔本西部乡下彻底退休。不得不说,那时候是一段惬意的日子,无忧无虑,胃口大好,吃饭总是仗着铁嘴钢牙,狼吞虎咽;用北京话就是牙口好,胃口就好,吃嘛嘛香。
直到有一天,我注意到我的牙没有那么齐了。
开始我也没有在意,照样我行我素,大吃大喝,大嚼大咽。慢慢地,我注意到牙开始疼了,牙龈有时还出血。
我于是谷歌了家附近的一个牙医诊所。我按照预约的时间到了那家诊所一看,又是印度人开的。除了前台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人姑娘,医生和护士全是印度人,不要说没有说中文的,连英语我听起来都困难,印度口音太浓重,听起来觉得更牙碜了。
我知道这个区印度人很多,华人诊所很远而且很难约。我想反正没什么大事,就近看看吧。
赶上接待我的是一个胖胖的印度大妈。我不是没有犹豫,但想到反正我牙应该问题不大,就让那个胖大妈看了。胖大妈一看,说我的牙没有大问题,都是牙菌斑,应该洗牙了,而且必须是深度清洗。
她说她正好有时间,问我是不是马上做深度洗牙。我觉得她的结论符合我的预期,应该洗了牙就没事了,就同意了。
我很快就对这个洗牙后悔了。可是已经晚了,胖大妈已经给我牙龈打了麻药,我只看见胖大妈在我面前挥舞不同的工具,有大钩子,刨子,钎子,伴随着高频振动,对我的牙又凿又刮又钩,还口中念念有词,我听明白主要是抱怨我的牙多么多么脏。我就觉得她把我的口腔当作了木工作坊,我口里都是血腥味。旁边的护士拿着水管和吸管忙不迭地边冲洗边吸吮。我这才明白,为什么刚才胖大妈一定要给我牙龈打麻药,否则这种洗牙不疼死我才怪。
这个深度洗牙进行了差不多一个小时。胖大妈和护士小姐都累的气喘吁吁。我也紧张的汗流浃背。总算完了。胖大妈给开了点止痛药。我付完钱就回家了。
胖大妈嘱咐我一天后就可以正常吃饭了。可是我不敢大意,连吃了好几天的流食。可是牙齿还是疼的厉害,靠止痛片缓解。而且我感觉嘴开始越来越肿了,牙齿也好像松了。我不敢刷牙,只能每顿饭后用漱口水漱口。
又过了几天,嘴好像开始消肿了,也不那么疼了。我就开始恢复了吃饭时的快节奏。为了慎重,当时还是只吃软食流食。
有一天,在我喝粥的时候,突然感到粥里有颗小石头,没控制住一下子吞到肚子里了。我正在纳闷怎么米里会有石子呢,突然嘴里感觉不对,出现了一个豁口。
我用舌头一舔,镜子一照,发现后面大槽牙掉了。
我又气又急,当时就认定那个印度胖大妈把我的牙弄坏了。哪里有那么狠的洗牙!我更担心那个坚硬的金刚后槽牙会在我肚子里造成后患。
我顾不上预约,立即开车到了那家诊所兴师问罪。前台小姐看我气急败坏的样子,没有预约也让我插了队。
等了不一会儿,我被护士领到了胖大妈的诊室。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,尽量用平静的语气把早已想好的话说了出来,既让她了解事情的原委,也暗含抱怨和威胁。
胖大妈又检查了一下我的牙,说我牙周发炎了,提出先免费拍个X光片子,看看怎么回事。虽然我不认为拍个片子会有什么用,但是一想反正是免费的就同意了。
过了一会儿,胖大妈拿到片子,兴奋地告诉我她的重大发现:我掉牙和洗牙没有关系,是因为我的“WISDOM TEETH”造成的。
我一听什么“智慧牙”?愣了一下,接着转瞬明白了,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智齿嘛!我不信,六十多岁的人了,还会长智齿?
可是我看到X光片,傻了。我看到我口腔左侧最里面,分别有上下两个发亮的大牙,完全横着长,正对着其它的竖着长的两排好牙,上面一个最近的后槽牙已经被挤掉了。原来我牙的毛病,都是这两颗智慧牙闹的。
面对着没有想到的反转,我哑口无言,顿时不好意思,只能向胖大妈道歉,表示要支付所有费用。那胖大妈说,智齿问题涉及拔牙和种牙,她这里做不了,必须找专家做。她会写一个REFERRAL信,把我介绍给一个这方面的专家。
我看到她的REFERRAL信写的是一个叫“ASHI MATHUR”的医生。我一看名字,应该是西人医生。就马不停蹄地预约了。我知道我的牙耽误不得。
到了预约那天,我早早到了专家诊所。前台让我填表然后等候。
我在等候的时候,看到墙上贴着这里几个医生的照片和简介。我发现这个“DR. ASHI MATHUR”是个印度老头,秃头,戴着金丝眼镜,留着白花髯胡,眼神透露一种高冷的表情。他的简介说,他有印度新德里大学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医学文凭。从医三十多年,发表N多论文,挂着十几个头衔,其中两个我记得很清楚,是“国际口腔种植协会ITI澳洲分会理事”以及“澳洲面部整形协会维州分会副会长”。单凭这照片和简介,阿西周身散发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气场。我心里踏实不少。
就是他了。为了方便称呼,我心中称他为“阿西”。
等我见到阿西时,他看上去比照片老得多。他看了看我的X光片,说上下两个智齿已经挤压了好的牙齿,造成了牙周炎,上颚尤其严重,靠近的大槽牙都被挤掉了,所以两个智齿都要拔掉,先拔上面那颗,然后再尽快种上那个掉的后槽牙,以便恢复正常咀嚼功能。上面牙齿搞好了,接着再拔掉下面的智齿,最后还要做全部牙齿矫正。
我听了连连点头,完全同意。可能是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原因,阿西的英语比一般印度人咖喱味英语顺耳的多。
阿西接着说,他的诊费每次是OUT OF POCKET 500元。我不知道OUT OF POCKET是什么意思,但是我知道每次500元诊费是够高了。为了拯救牙齿,我咬牙答应了。
然后,他又接着说,如果把上面的疗程都做完,你要准备至少10万刀的预算,大部分都不能用医保。我啊了一声,这折合人民币得五十万了,成本出乎我的意料。看到我犹豫不决的反应,阿西干脆地说,你要是没有钱,也可以只做一个疗程,或者找别的医生。我赶紧说,没问题,给健康投资是最值得的。
我当时的感觉就是,还没有躺到手术台上,已经是待宰的羔羊了。
没想到第一次拔智齿就出现了让我对阿西产生怀疑的事。
阿西显然很忙,除了看病,手术,还到处讲课。手术前的检查和文件签署搞完了一个月了,才轮到我拔智齿的手术。
记得那天我躺在手术台上,阿西匆匆进来,接过护士递来的麻醉针,一下子扎到我的下牙床上,扎完了才说会有点疼。
我等到他的第一针打完了,在麻药劲上来之前,得到说话机会。我赶紧说:”医生,您是不是扎错地方了,应该是上面。” 我指了指上颚。
阿西一下子愣住了, “哦,是的。不过,” 他反应很快, “一般都是下面智齿问题更大。你下面智齿早晚要拔,还是今天跟上面一起拔了吧?”
我想到女儿同时拔两个智齿的痛苦,做了坚决不同意的表示,同时心里有了种莫名其妙的不安。
于是,阿西又给上面智齿牙龈打了两针麻药,安慰我说打两针麻药拔牙就不会疼的。
果然拔牙时没有疼,但是我知道拔这个牙并不顺利。阿西用了很长时间,用了好几次电锯或电钻,发出来震耳的吱吱声,还伴随着BBQ的焦糊味道,让我有点毛骨悚然,然后我感觉他用钩子吭哧吭哧使劲钩撬那个牙根,我不得不使劲扭着脖子抗拒他的扭力,让头不动。护士在一旁一边用水冲洗创口,一边用吸管吸走口中的血水。我感觉像在一个屠宰场里。
在中途我还有几次感到阿西停了下来,不知干什么。透过防护墨镜,我发现他拿着一个相机对着我张开的大嘴拍照。
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阿西和护士一句话不说,只有他们越来越重的呼吸声,器械的撞击声,我嘴里的嘎嘎声,和我心里的心跳声。我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问题。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,呼吸加重,腮帮子已经累到失去知觉。
智齿拔出来的那一刻,阿西和护士都发出来胜利的欢呼。
在清理缝合创口的时候,我注意到阿西的手在发抖,不知是累的还是激动的。但他显得轻松多了,边缝边跟我解释,他从未见过我这么埋藏深又无比巨大的智齿,就好像他完成了一个有巨大成就感的创举。
等我手术完成站起来后,阿西问我疼不疼,我说不疼。阿西说幸亏打了三针麻药,好像他有先见之明。
他给我看了拔下来的智齿,确实硕大。我纳闷这么大的牙齿横在我的牙龈里几十年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本来想拿走这个大牙齿作为纪念,但是阿西说他要把这个智齿作为模型,写进文章里或PPT里,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并给他的学生上课用。我听了就不好管他要这枚牙齿了,但感觉有点怪怪的。
在我离开前,阿西给我开了抗生素、止痛药和消毒漱口水。嘱咐我两周后再过来复诊,并讨论种牙的准备工作。
我回家后,麻药劲过了,我体会到了女儿当初拔完智齿的感觉,疼得钻心,整个脑袋的下半部都肿了,吃饭睡觉都特别困难。经过两周小心翼翼地遵照医嘱吃药和保护牙龈,痛苦总算熬过去了。
两周后我如约来见阿西。阿西看了看我牙龈恢复情况,又给我拍了X光片。他说我的伤口已经愈合,但是这次掉牙和拔牙,牙龈上留了一个大坑。一般需要养三个月,骨头能把坑填满,但是我岁数大了,骨头长得慢,坑又太大,四个月以后再来见他。如果坑填的比较理想,就可以在掉牙的位置种牙了。
这四个月好漫长。我只能小心翼翼地用右边的牙嚼东西。刷牙也要小心翼翼。我还有意补钙和维生素D,希望骨头能长得不负我的期望。
熬到了见医生的那天。阿西医生给我拍了片子,看了一会儿,扭头对我说:很遗憾,你的骨头长得不好。而且你的上颚骨太短了,离鼻窦空腔太近。
看我有点懵,阿西把我叫到他的电脑前面,指着屏幕上的片子说:“你看看,这个坑的形状还在。你看上面,这个暗色的地方是鼻窦空腔,现在你上颚的骨头太薄了,没有办法种植牙。你这个位置的是最后一颗受力大牙,一边没有别的牙支撑,所以也不能做架桥(BRIDGE)假牙。”阿西无奈地摇摇头。
我一听就急了,怎么,我那就只能这样缺着一个大牙,左边用不了?一想到以后一辈子就只能用右边的牙,我都要哭了。
阿西看我着急的样子,想了一下,说:“不要着急。我给你上点骨粉试试。就是在牙龈坑里放上骨粉,过三个月,骨粉就能与上颚骨头融为一体。这样看看改善一下。”
接着,阿西拿出一张纸,在上面画了牙龈和牙齿形状,给我边画边解释:“但是即使上颚骨改善了,你的上颚还是太薄了,因为一在上颚钻孔就会打通鼻腔,一般的植体用不了。我给你用一种特殊的植体,是瑞士STAUMANN新研发的一种陶瓷植体,采用SLA表面处理技术,生物相容性比较好,与人骨的无机成分十分接近,参与骨组织的新陈代谢,促进骨头生长。而且,这个植体机械强度高,耐腐蚀,无刺激无毒,可以穿入鼻窦中使用。…….”他彷佛在学术会议上讲演。
看到我露出欣喜的表情,阿西接着说:“但是,这种植体需要根据你上颚骨的尺寸定制而且比较贵。像你这种情况,需要5000刀的额外费用。”
我一听有办法,就毫不犹豫地说:没问题。
阿西一看我那么痛快,就满脸微笑地说他知道我着急把牙做好,他要优先给我治疗,让我下周这个时间来加骨粉。同时,让我在前台交钱,他马上向瑞士方面定制我的植体。
一周后,如期做了加骨粉。没想到跟拔牙差不多受罪,把长好的牙龈切开,然后加入骨粉,再把创口缝合。
然后又是一周的抗生素,止痛片、漱口水。然后祈祷骨头长得符合要求。
等了三个月,终于迎来了种牙的大日子。阿西那里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也沐浴更衣,吃了一顿大餐,义无反顾地躺到手术台上。
阿西一脸凝重,却安慰我不要紧张,告诉我X光片显示骨粉已经发挥作用,上颚厚度已经达到要求,一切都会好,剩下的只是做一个惯常的小手术而已。
确实,接下去都是惯常:打麻药,切开牙龈,然后在牙龈上校准位置打孔。护士在旁边忙着一手拿喷水管冲洗,一手拿吸水管吸水。
可能是骨粉的效果太好了,我上颚骨密度变高。我透过防护墨镜看到阿西拿着钻机使劲往我脑袋里顶。我看到阿西脑门上浸出细细的汗珠,特别担心他打通上颚后收不住,一下子把钻头打到我大脑里。
还好,他成功打通了我的上颚,好像没有伤及鼻窦和大脑。
阿西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私人定制的高价植体,要把它安装到刚打好的骨孔里。这时不知怎么回事,一个硬物掉到我的喉咙眼上,阿西突然大叫“DON’T SWALLOW!”, 我吓了一跳,就着血水把那硬物咽下去了。
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,就听见阿西急切地问:“你把它吞下去了?”我一下子想到我不会是把植体吞下去了吧?
阿西不等我回答,就把我从手术台上揪起来,让我把那东西吐出来。那护士也手忙脚乱地扶住我,拍我的背。
可是,那东西已经到我肚子里了,吐出来的只是一点血水。
确认我已经把植体咽下去了,阿西反倒是镇定下来,满脸堆笑,和蔼可亲地安慰我说没事没事。然后他指示护士重新把我安置在手术台上,开始缝合我上颚刚切开的伤口。
干完这个,阿西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,一本正经地问我:为什么不听他的话,把植体咽下去?
我心想我哪里要把它咽下去了?可是我的嘴和舌头还麻着,心悸未定,根本说不利索。
阿西不等我申辩完,就说“这是你的责任,我们现在只有两个选择:一个是重新订购一个植体,要等三个月,另外付费。”
看到我震惊的表情,阿西接着说:“其实这种情况经常发生,不算什么。大部分人都选择把植体排泄出来,继续使用”。
看到我还是震惊的表情,阿西接着放软口气说:“这种植体十分坚固,不会被胃酸腐蚀,完全可以重新利用。干嘛不呢?”
我的脑子飞速转了一下,钱我肉疼,更重要的是我绝对不想再等了。于是我努力用发麻的舌头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选择第二个选项, 但是有个条件:你不能把这件事写到文章里或跟别人讲”。
阿西伸出手:“一言为定!”然后给护士打了个电话。
不一会儿,护士进来递给阿西一叠厚厚的文件。阿西把这个文件交给我,说:“这是这个事件的知情书和同意书,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个字。”
我一看那些密密麻麻、充满术语的蝇头小字就头大,索性作豪爽状,闭上眼睛签了字。
阿西打开一个抽屉,拿出一小瓶药:“这是通便便的药。植体很硬,有棱角,容易卡在消化道里。每天饭前吃一粒,几天之内必定会排泄出来。但是你一定小心不要让植体掉进马桶里。”
我接过药,纳闷他怎么在自己抽屉里常备这种药。
看到我满脸狐疑,阿西说:“拿到后清洗干净就好。我还会消毒,放心。还有,你现在鼻腔跟口腔是开放的,虽然我在钻孔里放了止血棉并缝合了伤口,还是相通的。所以你不要感染,不要感冒,不要流鼻涕,不要打喷嚏。”
最后,他给我开了一大堆抗生素,止痛片,再次叮嘱我一旦拿到植体就马上通知他,就让我走了。
我一回家就开始考虑和布置“回收”植体的事。首先,我知道吃了那个药一定是要拉稀的,因此想过要牺牲厨房洗菜的盆,放在马桶上拦截;但是觉得还是不保险,怕万一那个宝贝疙瘩掉到马桶里冲掉。于是我下狠心,收集了家里所有能牺牲的衣物和报纸,一叠叠铺在地板上。
都布置好了,我开始吃药了,那个药果然很猛,第一天就开始拉稀。每一次完事我都要戴上橡胶手套反复翻找,生怕漏掉。俗话说的真对,自己屙的屎不臭。
第二天,我坚持着边吃东西边吃药,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要蹲在一叠垫物上来一次。屙得我快虚脱了,那宝贝疙瘩还是不见踪影。尽管肚子明明空空如也了,还是觉得肚子老是不舒服,有闷胀感,里面有东西出不来,卡住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,那几天真是不堪回首。我吃不好睡不好,虚弱至此,还不敢感冒生病,精神上都要垮了。
第三天一大早,还没吃药就突然有排便的冲动,连忙找到地上的一叠纸蹲下,然后很明显地感到下面有硬东西出来了。我赶紧一看,下面有两个东西。我心一惊,莫不是那宝贝破成两半了?
当我把它们冲洗干净时,我才发现原来一个是我以前掉下的那个后槽大牙,另一个不是那个五千多刀的宝贝疙瘩又是什么!心中顿时大喜,好像中了巨奖。
我把失而复得的植体好好洗了几遍,还用漱口水泡了几个小时。也顺便把那个后槽牙也洗了,想留下做个纪念。
完后我就给阿西医生打了电话,报告这个重大喜讯。阿西听了也很高兴,马上安排了第二天的种牙手术,生怕那个宝贝又没了。第二天的手术有条不紊,波澜不惊,植体顺利植入,谢天谢地。手术完后,阿西向我表示祝贺,说手术很成功,植体很合适。等我种的植体与上腭骨长牢固以后,就可以取模做牙冠了。
阿西让我两周后来他这里复诊,千叮万嘱,这两周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植体。不用说,他又开了一堆抗生素和止痛片。我这辈子从未吃过这么多抗生素。
我在回家的路上,开车都慢慢的,生怕车子一颠就把脑袋里的那玩意儿颠出来。回到家后的两个星期,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感冒,生怕一打喷嚏,那玩意儿像子弹一样从鼻孔射出来。
漫长的两周过去了。我又来到阿西面前。
阿西检查了一下我牙齿的状况,告诉我说稳了,现在可以取模做牙冠了。我突然想起了什么,把那个作为纪念品的后槽牙拿给他看,只是觉得好玩。
阿西接过那颗后槽牙,端详了好一会儿,说它虽然有点失去光泽,但牙面釉质和形状,包括沟褶都基本完好,所以不用再来取牙模了,直接用这个真牙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牙冠,会跟周边的牙完美贴合,打磨都省了。说完他就把我的大槽牙放进自己的口袋。
还可以酱紫?我对阿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
后面的事情就乏善可陈了。现在,我的牙冠已经装上了。正如阿西说的,我的牙冠与周围的牙齿很贴合,没有任何不适感,跟牙没有换过一样。
可是,我知道我那个牙是不一样的。我每每想到嘴里含着一个那么有来历的东东,总有膈应的感觉。
关键是,阿西的诊所又催我去拔下面的那个智齿了。我有点为难。你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呀?
本文内容源自网络仅供参考,不作为诊断医疗依据,更多查询请 → 在线咨询客服